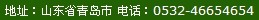|
汪顶松,男,安徽岳西县人,自由职业者。偶有小说及散文见诸省市级报刊杂志,小小说《与佛为邻》曾被选入年全国高考模拟试卷。 骚客 10. 从省内找到省外,又从省外找回省内,来回兜了一个圈子后,县作协总算是跟省城一家出版社谈妥了。二宝整理好书稿,把家里的一点积蓄搜罗干净,一并交了上去。夏莲香在电话里开玩笑说,看来出书跟出嫁差不多呢,都要挑挑拣拣的。二宝就说,我的书已经嫁出去了,你什么时候也把自己嫁了啊?夏莲香忽然就把电话挂了。没过几天,样书下来了。二宝一面惊叹出版社办事雷厉风行效率奇高,一面又气愤他们粗制滥造敷衍了事。样书封面是屎黄的底色,几个弯弯扭扭的黑字涂在上面,像快要断气的蝌蚪在粪窖里挣扎,怎么看怎么叫人难受。作者的相片印在勒口处,其技法深得法国印象派油画大师莫奈之神韵,影影绰绰的,叫人难以分辨;眉毛一浓一淡,嘴角一高一低,像是跟鉴赏的人调情。纸质低劣不说,油墨忽深忽浅,字体时大时小,诵读起来不啻结巴说话。“简直不像话!”二宝跑到石总编办公室,把样书递给他,“这叫什么东西嘛,盗版书都比它做得好!”“确实一塌糟,幸亏我没凑这趟热闹。”石总编翻了翻样书,笑着说,“这事我管不了,你去找马秘书长反映一下,丛书是他一手张罗的。”二宝撵到马秘书长单位的时候,马秘书长正歪在椅子上做梦。听明二宝的来意,作协秘书长伸了一下水桶腰,砸着嘴说:“刘老师你反映的这些问题我已经跟报社交涉过了,报社回复说印刷质量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至于文字上少量的错误或疏漏,因时间和人手的关系,肯定是在所避免的。如果作者本人要求严苛的话,可以亲自去出版社勘误。”“扯淡!”二宝恨不得要骂娘,“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回去打探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大半都说,无所谓啊,玩么,有什么好较真的呢。也有几个表达出了相同的愤慨,说书的质量代表的是作者的品位和修养,代表的是作者对待读者的态度,最马虎不得的。几个人互通心迹,相约去省城勘误。二宝临行的时候,心里惴惴的,似乎有什么事情搁不下,眼珠子转了好几圈,又想不起什么,只得作罢。到省城第三天,勘误几近尾声,报社的电话急急打了过来,说二宝他老子刘老头走了。二宝丢下书稿,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二宝踉踉跄跄闯回家的时候,刘老头已经躺在寿材里了。寿材停在供桌后面,中间隔着一帘暗红的挂布,上面爬满了蝇头小楷,写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里的句子。供桌上堆成了小山,金童银女分列左右,中间稳稳坐了一只拔了毛的土公鸡。一盘清蒸鱼,一碗红烧肉,一碟花生米,挤挤地摆成一排,都是刘老头喜欢吃的下酒菜。桌拐上点了一炷檀香,几根蜡烛插在青萝卜削成的烛台上,火苗一跳一跳的,落在桌子中央的相框上。相框里的那个人憨憨地笑着,眼睛在烛火里一闪一闪的,像是跟进出的人打招呼。桌子底下摆了两副三牲和一堆鞋,鞋子有新的,也有旧的,旧的都破得不像样子了。大宝跪在供桌旁,拖着清鼻涕往火盆里添香纸。成片的纸灰从火焰里腾起来,仿佛无数只惊慌的蝴蝶,满屋子乱飞。二宝扑通一声跪在供桌前的草垫上,颤着嗓子喊:“大哎——”刘老头听不见了,怎么喊都听不见了。二宝上次回来,那么轻地喊他一声,他都听见了,都稳稳地应了。这个时候,怕是睡着了哩。是的,永远地睡着了,怎么听得见呢?那个操劳一辈子的刘老头,这回总算踏踏实实地歇下来了,总算不用起早贪黑地摸索了。这两年,刘老头常把二宝他娘挂在嘴上,说做梦都想她,现在好了,现在终于可以天天跟她在一起了,再也不用叨念她了。可是二宝心里恨呢,恨自己没给大治病,恨自己没陪大多喝一口酒,恨自己没给大送终……有人搀二宝起来,二宝不肯,跪着往后堂爬。后堂人可真多,有站着的,坐着的,也有跪着的,都披麻戴孝,都哭作一团。二宝趴在寿材上,拼命地哭,拼命地拍打,拼命地掀棺材盖子。两个堂兄弟冲上来把二宝抱住,死死地抱住,劝他节哀。二宝两只脚乱跺,吼着说,我要看我大呢!我要看我大呢!后堂的人就哭得更厉害了。前堂的人听见哭,也都抬起袖子抹眼泪。不光是孝堂里的人,站在外面的人也是眼睛红红的,都在想,刘老头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招人喜欢的一个人,怎么招呼都不打一个,说走就走了呢?翠花红着眼睛进来了,她是从灶房那边过来的,油盐柴米,盘碟碗筷,她都得过问,不然来帮忙的亲戚邻里就找不着头绪,就越忙越乱。翠花见二宝回来了,就一把抱住自己的男人,哇的一声哭了。二宝矮下身子,把头拱在翠花怀里,抖抖地哽着嗓子,抖抖地搂住翠花的脖子。 “大哎——”两个人都哭,都喊。掌事的堂叔也进来了,他是来找二宝商量丧事的。二宝看见堂叔,还来不及叫一声,眼泪又涌出来了。堂叔比刘老头小不了多少,跟刘老头的关系好得很,心里也难受着呢。可是,都这个时候了,光难受又有么用呢?他得把老伙计的后事办好,得把老伙计安安稳稳送上山,这样才算对得起老伙计,才算对他有个交代。堂叔安慰二宝几句,就把办丧事的一些细节和程序跟二宝交代了一遍。以往,家族里遇见红白喜事,哪个不是刘老头拿的主意?哪个不是刘老头说了算的?现在,拿主意的那个人再也拿不了主意了,再也当不了家了,他自己的后事正让别人帮他拿主意呢,他的家正让别人当着呢。堂叔交代完,又安慰说,天王老子也要走这一路的,不要太过悲伤,免得坏了身子,你只管做你的孝子,守你的灵,大小事情自有我来安排。二宝下跪行了谢礼,又趴在寿材上呜呜地哭起来。傍晚,做法事的和尚跟吹喇叭的乐手来了,众人七手八脚撤了孝堂,布置道场。天完全黑下来了。天黑了就要游灯结社,这是做法事的规矩,无论和尚道士,都有这一出的。掌事的堂叔手执菜油浸泡过的香纸扎成的羊角火把,拎只香篮走在前面,沿途撒些纸钱,放几挂鞭炮,再洒上几滴酒,给亡魂引路。大宝手托莲花碗,二宝持经幡,戚戚地跟在堂叔身后。老和尚边敲铙钹边诵经文,乐手鼓起腮帮子呜呜咽咽地吹着喇叭,几十号人手捧蜡烛排起长龙,一路吹吹打打,屋前屋后绕了一圈。返回道场,屋子里已是人影幢幢,主事的老和尚身披大青袍,手摇小铜铃,开始给棺材里的人超度。两名副手一个敲锣,一个打鼓,合着老和尚的腔调抑扬顿挫地唱和。乐手歪着脖子,时不时吹上一气喇叭,安慰亡灵往西方极乐。二宝手持纸剪的经幡,踩着老和尚的步调跳八字舞。老和尚越走越快,铜铃越摇越急。二宝跑得晕头转向的,一不小心踩乱了半个步子,差点跟老和尚撞个满怀。一通法事下来,两个人都气喘吁吁的,累得腿脚酸软。喝了两杯茶水,又歇息一会,换上了一名副手。大宝也替下二宝,亦步亦趋地跟在副手后面,一面绕棺材转圈子,一面由副手唱偈,以劝慰亡人,安抚生者。二宝趁机走到堂屋外面,看一看天,透一透气。外面起了微风,有些冷。天上挂着几片残云,一粒孤星嵌在云缝里,闪着冷光。和尚们超度亡灵的经声如歌似泣,乐手的喇叭呜咽低沉,在透着无限悲凉和孤寂的夜色里交织,盘桓,听上去格外叫人忧伤。 11. 乌米庵一带的风俗,过了头七,丧事差不多也就结束了。二宝空空落落地望着重新收拾后的屋子,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大在,日子一天一天往前过,习惯了;大不在,日子一天一天往前过,不习惯了。虽然这种不习惯的感觉是轻飘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像根附在贴身衣服上的芒刺一样,时不时提醒着它的存在,时不时影响着二宝的情绪。报社的同事,县城的一些朋友,在刘老头上山前的那些天,都去吊唁了,都随礼了。这是人情,也是面子,二宝心里存着感激。回到县城,二宝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挨个地致谢,挨个地回礼。回礼也是要随俗的,一包香烟,一条毛巾,很简单。二宝到香香酒楼找夏莲香的时候,夏莲香打扮得很精致,精神也很好,但不是以往见到二宝时容光焕发的那种好,不是千娇百媚的那种好。现在的好,是一种出于职业习惯的彬彬有礼的好,是一种能让人产生距离感的好。两个人简单聊了几句刘老头的后事,夏莲香就安慰二宝,叫他节哀顺便。二宝客客气气道了谢,送上薄礼,准备起身告辞。夏莲香望着二宝,犹豫了一下,说:“胡老三跑了,卷走了一笔款子。”“跑了?”二宝眼珠子快要掉了,“什么时候跑的?”“伯父刚去世的那会子,所以没告诉你。”“卷走了多少?”“三万多。”“三万多啊——”二宝出了一身汗,结结巴巴地问,“报警了吧?”“没有。”夏莲香摩挲着手背说,“你把他当做亲弟弟一样,我怎么可能报警呢?”“狗日的!”“骂人有什么用?”夏莲香说,“只怪你遇人不淑,摊上这么个好兄弟!”“我瞎了眼!”二宝不敢与夏莲香对视,“那笔款子要是追不回来的话,我来还。”二宝说这句话的时候,底气不是特别的足。他心里清楚,就凭自己那点死工资,不吃不喝的话,也要还上个三年两载。就算有钱去填那个窟窿,翠花那边怎么交代? “算了吧,算我少做几单生意好了。”夏莲香笑笑,“你放心,这点损失我还是扛得住的。”从香香酒楼出来,二宝像个大病初愈的人,头重脚轻的,没有一丝气力。这时他才想起胡老三没有回乌米庵帮忙办丧事,没有送大最后一程。胡、刘两家好得跟一家人一样,照理,胡老三也是要戴孝的,也是要守灵的。他没有。他不是人哪!他辜负了他的兄长,辜负了他的老板,卷走了款子,跑了。他招呼也不打一个。他是白眼狼哪!一连几天,二宝都木呆呆的,像丢了魂一样。同事们以为二宝悲伤过度,私底下都夸他是个孝子。只有会计储大姐照样没轻没重的,站在走廊上大呼小叫地喊二宝接电话。 “哥,我对不起你!”电话是胡老三打过来的。“你个混蛋!”二宝嗓子有些发抖。“我混蛋!”胡老三抽了自己一耳光,“我没有回去送刘伯,我该死!”二宝头毛杪上窜出火星来了,大吼说:“你做了更该死的事!”他恨不得从话筒里伸手进去,把胡老三从电话那头拽过来,狠狠揍他一顿。“哥,小满那骚货把我害了!”胡老三又抽了自己一耳光,“那个臭婊子把营业款输了个精光,找不到人了。我没脸见你!我混蛋!我该死!”“你现在就给我死!”二宝拍着桌子喊,“早跟你说过,那女的不是好东西!现在好了吧?后悔了吧?你个王八蛋!”“我王八蛋!”胡老三拖着哭腔说,“哥你跟夏老板说一声,我对不起她,她的钱,我一定还!”“你活该!”“哥,刘伯满七七的时候,代我磕个头,烧刀纸……”胡老三哽咽得说不出话了。“死去吧,你个狗日的!”二宝青着脸皮回校对室的时候,正好碰上石总编从里面出来。“正找你呢,生谁的气哪?”石总编问。“没呢。”二宝勉强笑笑。“没有就好,跟你说个事。”“么事?”“你的书下来了,叫你去领书哪。” “啊,谢谢!” 二宝把新书领回来,放一些在夏莲香书店里,又带了几本回乌米庵。翠花扬眉吐气地散给亲戚邻里,还说等二宝老子满七七的时候,要在他坟头上烧一本。余下的拉回宿舍,堆成了一堵墙。二宝打小就喜欢书本上散发出的那股令人愉悦的油墨味,觉得世上再没有比油墨味更好闻的味道了。他常常沉陷在那股奇妙的味道里,忘却了时间,也忘却了自己。现在,他的床头上,他的写字桌上,他的衣柜里,宿舍里的每一个缝隙里,都充斥着那种味道。现在,他的鼻腔里,他的嘴巴里,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散发着那种味道。现在,他的梦里,他的意识里,他的每一根神经里,都填满了那种味道。那味道无处不在,那味道如影随形,那味道挥之不去,那味道让他喘不过气来了。狗日的油墨味!去他娘的油墨味!被油墨味困扰着的二宝想起了唐部长曾经提起过的文学创作基金的事。他前后跑了三趟,才找到陈副部长。陈副部长年纪很轻,说气话来也客气。“这个事嘛,唐部长是嘱咐过我的。”陈副部长客客气气地说,“刘老师你可能不知道,申请基金的作品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原创作品;第二,必须是公费出版;第三,必须是发行量不少于五千本。以你刘老师的情况来看,这个忙我恐怕是想帮都帮不上了。”“听说好像没这么多门槛啊,是吧?”二宝问。“刚开始要求不是很高,后来申请的人太多,条件就苛刻起来了。”陈副部长说。“听说申请的人好像也不是很多啊,是吧?”二宝问。“多着呢,头都挤破了。”陈副部长说。 “听说要活动活动才能申请上啊,是吧?”二宝问。“刘老师真会开玩笑,哪有的事嘛!”陈副部长严肃了。“听说跟我一起出书的,好像有人申请上了,是吧?”二宝问。“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陈副部长好像生气了。“听说申请上的好像是两个人,是吧?”二宝问。“刘老师你哪来的许多‘听说’许多‘好像’呢?都是胡说八道!”陈副部长真的生气了。“有别的法子不?”二宝问。“不好意思,确实没有法子。”陈副部长摊开两手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指望了。”二宝说。“既然这样,那就算了。”二宝又说。“既然这样,那就不打扰您了。”二宝最后说。 12. 夏莲香建议二宝邀请本县几位重量级的作家来压阵,大张旗鼓地搞一次签售活动,好把图书销量搞上去。二宝有些心动,转念想,自己又不是什么出了名的人物,知道他的人比知道蚂蚱几条腿的人还少,知道他是作家的人更是少而又少,万一到时候没几个人来凑热闹,那就尴尬了。“扔了那么多钱进去,总要想法子赚回来。”夏莲香说。“慢慢来吧。”二宝说。“你看着办吧。”夏莲香稍稍停顿了一下,语气忽然有些沉重了,“你知道不,牛主任进去了。”“进去了?”二宝问,“去哪里了?”“纪委,双规了。”“不会吧——”二宝结结巴巴地问,“么事啊?” “他们说是经济问题。” “么时候进去的?”“昨天。”“怎么会这样啊?”二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前几天校样的时候,还校过他的稿子呢。” 二宝见过一些世面,知道像牛主任那样的人,别看平时风风光光架子十足的,一旦被纪委盯上,大半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牛主任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呢?二宝有些发蒙。“晚上一起吃饭吧,行不?”夏莲香把话题岔开了。“就我们两个人。”她又补充了一句。“我啊,恐怕没时间哩。”“今天我生日呢。” “是吧,生日快乐啊。” 跟夏莲香打完电话,二宝潦草把手头上几件要紧的事处理好,就早早下了班,跑到鲜花店逛了一趟。二宝从未给人献过花,也没有买花的经验,红着脸支吾了半天,花店老板娘还是没有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你到底要什么花?”老板娘有些不耐烦了。是的,到底要什么花呢?那么多颜色的花,红的,粉的,蓝的,黄的,白的,紫的,一朵朵娇艳欲滴,一朵朵簇拥在一起,挤满了整个屋子。那么多好看的花,长喇叭似的,五角星似的,绣球似的,盘子似的,一朵朵赏心悦目,一朵朵摇曳着身姿,都在冲他微笑,都在冲他打招呼。到底选谁才好呢?“你要是送给女朋友呢,玫瑰啦,水仙啦,三色堇啦,玉米百合啦,都可以的。送得最多的自然是红玫瑰啦,怎么送,送多少朵,也是有讲究的。”老板娘说完瞟了二宝一眼,又说:“不对啊,看你的样子,好像不是处对象的年纪了。你倒是讲清楚,到底送给家人还是朋友,男的还是女的?”“这个嘛,怎么说呢?”二宝脸红得更厉害了。“随便,随便什么花吧。”老板娘取了一束荷兰郁金香,一边包扎一边说:“我看还是选这个吧,什么场合都用得上。”从鲜花店出来,二宝一路把头压得很低,生怕被熟人撞见了。他觉得自己手里捧着的不是郁金香,而是一桩不可告人的罪证,越看心里越虚。香香酒楼冷冷清清的,接待员小金站在吧台后面打着哈欠,神情落寞得很。“刘老师是来找夏老板吗?”小金问。“她不在呢。”“去哪里了?”“下午被几个自称纪委的人请过去了。”小金犹犹豫豫地说,“说什么协助调查。”二宝脑子里一阵凌乱,乱得有些手足无措了。他拖着腿朝门口走了几步,发现郁金香还在手里,就又回转身,把那束花放到吧台上,笑笑说:“这花,送给你吧。”“谢谢!”小金有点害羞的意思,“谢谢刘老师!”二宝是在三天后才见到夏莲香的。夏莲香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刚装修好,既时尚,又阔绰。二宝第一次去夏莲香的新房子,进去后的第一印象就一个字:大。那么大的房子,一个人住在里面,一定很寂寞的。二宝想。夏莲香亲自下厨,炒了两个菜,一荤一素,又煲了两个汤,一素一荤。二宝望着热气腾腾的菜和汤,由衷地赞叹起来:真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哪,不仅人生得精致,菜烧得也精致!“来,喝吧。”夏莲香举起高脚酒杯晃了晃,“喝他个一醉方休。”夏莲香举止优雅,得体,妆也画得很好,但二宝还是看出她的憔悴来了。无论是啜饮时微微蹙起的黛眉,还是垂首时不经意间发出的叹息,都能显出她的憔悴来。二宝涌起一阵怜惜。怜惜过后,又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轻轻扎了那么一下,隐隐的疼。“一醉方休。”二宝说。两个人喝的是红酒,浅浅地斟在玻璃杯里,像批改作业时用的红墨汁。二宝素来喜欢白酒,性子很烈的那种。在他看来,红酒之类的东西虽然挂了酒的名号,压根算不得酒,顶多也就是含酒精的饮料吧。二宝望着红色的汁液一口一口送入夏莲香嘴里,就想,红酒,佳人,其实也挺好的,挺般配的。“这个地方我再也不想呆下去了。”夏莲香迷离着眼睛说,“刘二宝你不知道,我真的一天都呆不下去了。”“你喝多了。”二宝说。“我没喝多,一点也不多,我清醒得很。”夏莲香说,“刘二宝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太累了,比我想象的累多了。”“你喝多了。”二宝说。“我没喝多,一点也不多,我清醒得很。”夏莲香说,“刘二宝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太让我伤心了,我的心都碎了。”“你喝多了。”二宝说。“我没喝多,一点也不多,我清醒得很。”夏莲香说,“刘二宝你不知道,你他妈的太让我失望了,你他妈的不是人!”“你喝多了。”二宝说。“我没喝多,一点也不多,我清醒得很。”夏莲香说,“刘二宝你不知道,你他妈的狗屁都不如,你他妈的就是王八蛋!”“你喝多了。”二宝说。夏莲香真的喝多了。她的舌头变粗了,说起话来含糊不清了。她的脸像涂了油彩,泛着红光。她头重脚轻。她浑身燥热。她想站起来。她想扑进对面那个男人怀里。她想咬他,掐他,抓他。她想把他一片一片撕裂。她到底没有站起来。二宝站起来了。他知道,再喝下去的话,夏莲香会醉得一塌糊涂。醉得一塌糊涂的夏莲香有可能想发生点什么的。自打当初拒绝夏莲香以后,他就不再指望跟夏莲香发生点什么了。他的脚下有根红线,一头栓着颗道德的地雷,一头栓着颗婚姻的地雷,只要稍稍碰一下那根红线,两颗地雷轰的一下就炸了,会把他炸得粉身碎骨,炸得永世不能超生。他知道,再不走的话,他就有可能碰到那根红线了。“我该回去了。”二宝说。“我还没喝够呢。”夏莲香大着舌头说,“你不要走,我还没喝够呢。”“时间不早了。”“你不要走,你要陪我喝。”“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好吧,你走吧。”夏莲香吃力地抬起头,微微笑了那么一下,笑的样子很难看。“你走吧,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她软软地挥了一下手,见二宝真的要走了,忽然垂下手腕,抓住二宝的衣袖,用两只通红的眼睛死死盯住二宝,“外面都说我跟姓牛的有一腿,刘二宝,你信不?”“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二宝小心抽开袖子,匆忙离开了夏莲香。当房门慌乱地合上时,他听见屋子里有呜呜的哭声。 13. 腊月底下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一开始是零零碎碎地下,一片隔着老远一片,一阵隔着老远一阵,扭扭捏捏的,像极了矫情的女人。这样磨磨蹭蹭下了好几天,眼瞅着就要过年了,零星的雪花忽然化作漫天的粉团,劈头盖脸没完没了地往下洒,洒成一张又肥又厚的地毯,白晃晃的,无边无际铺展了开去。山峦,田野,房屋,街道,统统伏在那张地毯下面,只露出圆润而又模糊的轮廓,看上去既安静,又柔和。 天擦黑的时候,有人气势汹汹地擂二宝的房门,像要打架一样。二宝晕头晕脑地把门让开一条缝,一个女的堵在门口,披着一头的雪。瞪大了眼珠子看看,认识,自己媳妇呢。二宝一下子清醒了。“二宝,你没事吧,啊?”翠花挤进屋子问。屋子里腾着一股油墨、酒精和臭袜子混合而成的怪味道,地上到处是酒瓶子和纸烟头,乱得不成样子了。二宝裹着一身酒气挨床沿坐下,弓起腰,吧嗒吧嗒抽闷烟。“你到底怎么了,啊?”翠花抓住男人的肩膀,使劲问。见二宝不吭声,就摸他的额头,摸了两下,语气就缓了些:“我当你病了哩,害得我一口气从家里撵过来!”天没亮,翠花就撵过来了。大雪封山,通不了车,翠花就在胶靴底上缠上几圈草绳,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走了一整天。以往,二宝三天两头就往家里打电话,最近呢,一个多礼拜都没听到他的声音了。这就不对头了。翠花忍不住往报社挂了个电话,一个女的捏腔捏调地把声音递过来,说二宝窝在宿舍里睡大觉。睡觉?大白天的睡什么觉?病了?翠花还没问完,那女的就把电话撂了。翠花心里慌慌的,眼皮子也不安分起来,乱蹦乱跳的,瘆得很。半夜刚合拢眼,就开始做梦,梦见二宝躺在病房里,要死不活地望着她,一下子把她惊醒了,惊出一身汗。翠花待不住了。哪怕雪再大,路再远,她都要到城里去,去找她男人,找伢仔他老子。“翠花,”二宝忽然捉住翠花的手,沙哑着喉咙说,“报社,报社他妈的把我下了!”“下了?”翠花腾出一只手插进男人草窝似的头发里,睁大眼睛问。“凭么事啊!”二宝不说话,肩膀一闪一闪的,头也勾得更厉害,都要插裤裆里了。翠花贴着男人缓缓坐下,那只手还搁在他头上,慢慢往下摸,一直摸到脊梁骨上,又轻轻地拍。二宝脊梁骨硬邦邦的,没有肉。二宝瘦了,就这么些天,掉了好几斤肉哪!翠花眼睛潮潮的。“下就下了,又不是天塌下来。”翠花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回到乌米庵照样有饭吃,教教书,种种田,喂喂猪,快活得很哩。”二宝还是一抖一抖的,还是把翠花的一只手攥在手心里。这些天,他伤心够了,憋屈够了,失落够了,孤独够了,他妈的受不了啦!他妈的要发疯啦!他呜的一声哭了。直到上个礼拜,二宝才知道自己被下掉了。之前那几天,同事们都怪怪地背着他咬耳朵,怪怪地望着他,怪怪地跟他说话。二宝心里被搅得怪怪的。等到石总编找他谈话的时候,那种怪怪的感觉一下子发酵开了,发酵成一阵尖锐的痛。“小刘啊,今天把你喊过来,是想跟你谈个事。”石总编拿着派头说,“报社的情况你是清楚的,越来越不景气了,再这样下去,大家伙儿只有喝西北风了。怎么办?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才能发展。改革么,说白了就是动刀子,割阑尾割包皮割痈疽,割掉肌体里一切冗余的东西。你小刘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工作起来勤勤恳恳,这都是明摆的事。但是呢,按照宣传部的指导意见,你小刘是这次改革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编制不在这里,你不是报社的正式工,所以我们只能按程序走,请你理解和支持。”二宝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像成千上万只蜂子在里面乱飞,乱叫。牛主任出事的时候,二宝就感觉有些不妙了。他找过牛主任几次,想早一点把编制的事情解决掉。牛主任每次都打着官腔说,急么事嘛,人事局和宣传部那边还没协调好呢,年底争取解决。还没等到年底,牛主任就进去了,编制的事,黄了。只是没有想到,自己担心的事,竟然变成真的了,竟然这么快就来了。“啊,是吧。”二宝浑身轻飘飘的,说话的声音也轻飘飘的。“储大姐也不是正式的吧,还有小赵小孙他们合同工都算不上呢,也都下了?”“这个嘛,怎么说呢?”石总编摸了摸鼻子,“改革也不是一刀子切,也不是没有一点人情味嘛。老储一把年纪了,你叫她到哪里讨饭吃?不像你,你小刘好歹还有退路,还有书教,对不?小赵小孙他们年纪轻,是报社的有生力量,也是报社重点培养的对象,暂时不予考虑的。”“这么说,下掉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动刀子么,总得找个地方开口子不是?”“知道了,”二宝寡白着脸说,“我懂了。”二宝说完,扶着桌子站了起来,眼睛直直地瞪着石总编。“你要做么事?”“不做么事,去屙尿。”二宝真的是屙尿。这泡尿夹得有点久了,屙起来憋屈,愤懑,打冷颤。他的心也在打冷颤。唐部长退休了,他后面没人了。牛主任出事了,他成多余的人了。作协主席选牛主任了,他成眼中钉了。他什么都明白了。好不容易混成半个城里人,才混一年,就跟这泡尿一样,憋着劲屙一阵,到头了。命哪!翠花进城的第三天,雪驻云散,煦日高照,亮晶晶的地毯在变薄,在萎缩。山尖冒出来了,房屋冒出来了,河水撕开了一道又一道口子,汽车横冲直闯,把街道辗压得伤痕累累。整齐干净的地毯一下子支离破碎起来,一下子污浊不堪起来,活像一块又脏又旧的破抹布摊在日头底下。二宝上街约了辆摩的,准备明天一早把行李拉到车站去。回宿舍的时候,看到路边有家废品回收站,就袖起两手,拐进去转了转。晚上收拾东西,翠花一边打包,一边望着靠墙的那排新书,问二宝:“这一大堆书怎么办?”二宝也不抬头,撅着屁股说:“卖掉吧,两毛钱一斤哩。” 真小说所有小说,皆由作者投稿和授权,原创首发,禁止转载。 真小说,真的不能小声说。 赞赏 人赞赏 哪家医院白癜风能治愈北京哪家医院治白癜风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dikaiguan.com/hlbsp/hlbsp/7334.html |
当前位置: 黄萝卜_黄萝卜食谱_黄萝卜挑选 >汪顶松短篇小说骚客三
时间:2018-3-1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早餐小吃做法各种饼的做法真美味,留着慢慢
- 下一篇文章: 寿司专业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