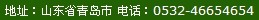|
陇上日月(7) 幽幽南山
陇上日月 7.晌午 天亮的有些迟,黑的也早。这几天,饭吃的有顿数了,觉也睡的踏实,家里的炕也被锁子婆娘烧热了。由于天天干活扎捆当归和削切胡头,腿上穿的单裤也没感觉到有冷风钻进来的。可能是坐着干活的缘故吧?坐着的时候腿是曲着的,偶尔伸展一下活动活动酸麻。 在我削切当归胡头的时候,好几次看见锁子婆娘背一个很大的背篼,出去在房后的旧麦场里干其它活,旧麦场里是堆积麦草和其它作物秸秆的地方。周围被挖开来种了甜菜,还有几窝番瓜和豆角,两个月前我路过的时候,顺手摘了一根嫩番瓜,就像啃黄瓜一样地生吃到肚子里。同样都是瓜,西瓜、黄瓜都是生吃的瓜,这番瓜就得炒熟了才能吃,那根小番瓜被我生吃了后,胃里往上泛了一下午的酸水,最后蹲在离平桥头不远的树窝里吐了,害得我吃过的一个油饼也一起吐了出来,想起被一起吐掉的那个油饼,我心里就痛。原来这几天我睡的热炕,是锁子婆娘拿她家旧麦场上堆的碎麦草烧的,那温温热热的感觉真让人不愿起来,要是吃饱肚子了睡上一整天多美。不行,再喝上一罐煮得浓浓的红枣茶再睡。现在肚里有食,睡觉也有热炕,休息的好就精神好,精神好干活也就快,干活快这时间也就过的快。而且还有锁子婆娘晃来晃去的身子在眼前转悠,唯独没变的就是锁子灶窝母鸡一样地咳嗽声。前前后后十一天,锁子家的当归终于捆扎完了,胡头挂在房檐上着哩,房檐椽头的钉子是我新钉上去的。厅房和侧面东房的房檐上都挂满了串好的胡头。一串一串的特像西游记里沙僧脖子里的素珠,厅房窗台下一溜子码放得整齐的葯把子。我自己看着都感觉自己这次干了个人活,感觉自己甚至有些伟大。 裤子膝盖上磨破的地方露出了黑肉,下巴上几根发黄地胡子稀稀拉拉如老鼠的尾巴,站在院子里噼啪噼啪地拍了一下自己的手。这手掌,跟脚后跟没啥两样,要是摸一摸兰州亚欧商厦卖的缎被面子,估计都能挂出一撮丝来。这手,这手猛地一下子杵在尕秀熟睡的怀里,估计扎得尕秀一蹦子能跳着仰尘(天花板)上。想到这,我自个都失笑地笑了,扑哧一下,把脚跟前寻食的鸡惊得翅膀一拍,闪了三四尺远。鸡地惊跳让我神情又暗淡了下来,这几天钱寡妇怎么过活呢?粮食淘下了么、猪薏子粉碎下了么?想到这,我再没心思等着吃锁子婆娘尕秀做的晌午饭。“锁哥、嫂子,我家里房上有一页瓦破着哩,我走了,我借个梯子了换换瓦去,不然下雪了就头顶上猴浇尿哩。”其实锁子家就有一架梯子哩,这几天往房檐上挂串好的当归胡头一直在用,我没说借他家的梯子,我根本不是去换我家房上的瓦,而是找借口得个空了去寡妇家看看。我说着话的时候探头朝厨房门里瞅了一眼。“我的呱天神啊!你不能走,这长饭刚擀好,正勾臊子汤汤着哩,老三,你把嫂子当外人着哩么?”尕秀提着个铁勺,急忙赶三的从厨房里蹿了出来。炕上的锁子急得“咳咳,他三爸,你就把饭吃了,下雪也不是这三五天,你进来我给你说,咳、咳。”尕秀两只肉呼呼的手,从脊背后面连搡带推地把我按在了厅房里的沙发上,垛了一下脚,又拿水汪汪的大眼睛剜了我一眼,随后一转身就出了厅房门。看着炕上干着急又说不出话的锁子,我说:“锁哥,我不走我不走,我还要陪锁哥拉家常哩么,给锁煨一罐茶哩么。”我边说话边拿挂在烤箱烟筒边上的钢筋勾子掀开了炉盖,从快架空的碳块中间往下捅了一下,枯騰騰的一股黑灰冒出后,碳堆中间红火苗呼闪呼闪地升了起来,我嘴里不由得说:“人心要实哩,火心要虚哩么。”“咳咳,就就是”炕上趴着的锁子额头上青筋像曲蟮(蚯蚓)一样弯曲着,每咳嗽一声,锁子的身子就像虾一样弯曲一下,看得我心里倒有些发酸。捏了美美一把茶叶,捣进茶罐里,茶叶冒得像出沿的麦摞子,我又三个指头从茶罐里撮出了一撮。注了没有眼泪多的一点水,茶罐就冒泡了,看来还得掏出半把茶叶,真想着到厨房拿双筷子,从茶罐里往出来夹茶叶哩。锁子婆娘尕秀端着一个二尺见方的大红木盘进来厅房,把盘子在茶几上一放。有油泼辣椒,醋,半小碗蒜泥。一小碟切得如头发丝一样细的黄萝卜,还有一大碗麻菜,麻菜用熟油炝过的,上面翠绿翠绿地几小节嫩葱丝。 从盘子里拿出几样子后,锁子婆娘尕秀用手指头刮了一下泼到碗沿上的一滴清油,顺手把刮过碗的食指在嘴里吱溜的一吮,又偏着头看了看盛黄萝卜丝的碟子,端起碟子撩起围裙抹了一下碟子的底子,这才出去到厨房下面去了。我直楞楞的半天没回过神来,这锁子婆娘一连串的动作麻利又自然,还有些熟悉,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这样的动作。是不是过日子的女人们都是这个样子?正当我愣神从脑海里搜寻这似曾熟悉的动作的时候,尕秀从厨房扯着嗓子喊:“他三爸,你先吃小菜,饭马上就好了,你先吃小菜。”这时的我,感觉自己不是自己,可不是自己又是谁呢? 村主任? 支书? 还是县一中教书的美女老师王四眼? 都不是? 我就是我,第一次被人这样抬举,第一次被人感激不尽的说着由衷的心里话,第一次让人当老君爷一样的供着……我的鼻孔有些酸痒,眼圈感觉到湿润了起来,听到厨房门口有脚步声,我赶紧拿自己脚后跟一样的手掌揉了揉眼睛,炕上侧躺着的锁子他是没有看见我这会的样子。转眼之间,锁子婆娘尕秀已经又端了刚才那个木盘进来,两个大白瓷碗里,切得细如席篾的面条,上面浇着浓浓的臊子汤。切成小丁的黄萝卜黄的是那样好看,几叶翠绿的菠菜、还有白白的豆腐丁和西红柿丁。碗还没有从盘子里端起来放到茶几上,臊子面特有的香味已经从我鼻孔里蹿到喉咙里下去了,我脖子里的喉结又不自觉地上下蠕动了一下。我偏着头欣赏着这两只细瓷白碗,碗外面淡淡的一族浅蓝色的兰花图案,整个碗的边沿没有一个豁口。在农村庄户人家里,由于大锅台做饭,洗锅的时候把所有的碗碟都一股脑地和在一起洗,难免碗碟的边沿有大大小小的豁口残缺。就连县城高二的馆子里,所有的碗碟都有小豁口,我就几乎没见过边沿整齐光滑的几个碗碟。尤其街边小吃摊上的碗,简直就像城墙的垛口,我甚至怀疑那些包了金牙的人,吃完小吃后偷偷地啃一下人家的碗,试试自己金牙的攻击力度,说是金牙,其实都是锃亮的钢色,有些也看起来威武的很。不过现在的好多小吃摊点,大多给碗碟上套一只塑料袋,顾客吃完后取下塑料袋就扔了,省去了洗碗洗碟的麻烦,顾客也乐意这样,起码看起来卫生一些。“他三爸,你赶紧趁热吃,今早刚灌的新醋,麦麸醋,你调上了吃看香着没有?我现在笨得不会做饭了么。”“哎吆嫂子,我还没饿么,赶紧给我锁子哥先调上一碗让吃,我早上让你添的搅团太多了,这会还感觉饱着哩么。”“饱啥哩?就是早上吃了石头瓦渣,干了这么多的活也颠饿了,你赶紧吃,我给锁子下一碗煮得绵一点的,你赶紧吃,吃完了把那一碗也添上,小菜也吃,再没有好些的菜做小菜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这么阔气的饭食在平日里几乎很少吃,很多少平常做了嫌麻烦,买些机器做的面条就成了,再说现在的年轻女人会擀好面的少之又少。只不过现在的年轻女人大多都识字,好多也上过高中。不像村子里的老婶婶们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尤其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视里的女人哭,她们也跟着掉眼泪,电视里的女人笑,她们也跟着笑。吸溜吸溜的很快一碗臊子面下了肚,用筷子挑起第二碗添到自己刚吃过的碗里,第二碗的面条有些往一起粘,我用筷子抖了抖就散开了,这长面可真柔。第二碗我吃了几口的时候打了个饱嗝,一打饱嗝我不由得想钱寡妇的儿子,只想让锁子婆娘尕秀再下一碗臊子面了我给端上送过去。“他三爸,你别光吃面,菜也吃,把新醋多调上些,菜多吃些,叫尕秀给你再下一碗。”锁子的话让我把刚才的念头打消了下去,再说我也不好意思给尕秀说让给寡妇的儿子端一碗面的,即就是我端面送去了,寡妇会不会让儿子吃锁子婆娘做的饭。这时候我幻想着寡妇的儿子蹦蹦跳跳地跑锁子家门口来玩,这样我就名正言顺的喊那个机灵鬼进来吃饭。那个小机灵鬼,有时候我拿从房檐下掏来的小麻雀,换他双面写过字的废作业本,我是用废作业本的纸,裁成一寸宽的条卷烟渣抽的。有时候从街上收工回来的时候,遇上路边别人家的墙头有伸出来的杏子或梨,就跳个蹦子伸手摘下来几颗,自己吃一两个,其余的给小机灵鬼留下了。村里人故意笑话着让小机灵鬼把我叫“爸”。小机灵鬼一听别人这样戏谑自己,就低头不吭气了,等别人不防备的时候,抓一把土扬在那人的头上撒腿就跑。有一次我带小机灵鬼在村子外的小河里摸鱼,小家伙问我他爸去哪儿了?我吱唔了半天没敢说实话,让他回家问他妈。小家伙说他问过他妈,他妈说他爸死了,他又问他爸埋在什么地方了,结果倒挨了他妈的一顿揍。我说那以后我给你当爸,小机灵鬼吐了一下舌头,说我要是有本事的话去给他妈说去。其实我也不敢给钱寡妇说这样的话,我一个人都过的恓惶,加上娘儿俩个,我真还有些信不过自己。但心里老想钱寡妇,想钱寡妇的那种感觉,和想锁子婆娘尕秀的完全不一样。至于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我自己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老有一种牵挂在寡妇身上,但寡妇老是爱骂我,怎么难听就怎么骂,骂完我还能吃上几个煮熟的苞谷或者烙好的馍。“咳咳,他三爸,你把烟点上了抽,要喝面汤了让尕秀给你舀一碗,吃完捞面再喝一碗面汤舒坦的很么,咳咳。”“锁哥,我啥都不喝了,你早些缓着,我也回去了早些睡。”我回应完锁子的话,起身就抬脚跨出了厅房的门,走到院子里也没有大声喘气,急急的就出了大门。(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郭亚军(幽幽南山)甘肃人,七十年代出生在渭水源头的一个小山村,喜欢文字,现就职于兰州一家名表公司做售后维修工作。 作家平台(白癜风治疗中药有什么北京治疗白癜风的费用多少钱
|
当前位置: 黄萝卜_黄萝卜食谱_黄萝卜挑选 >陇上日月(7) 幽幽南山
时间:2016-11-1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疯掉!能在花城汇立足的10家人气超高的食
- 下一篇文章: 蔬菜的六种错误吃法,有损身体健康